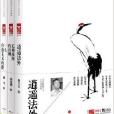
梦路书系
梦路书系第一辑:贺卫方《逍遥法外》,北大教授贺卫方十年思考精粹文集:针砭时弊,讲述人生,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妙语连珠。冯克利《尤利西斯的自缚》,管窥西方当代思想体系,堪称“西方政治思想地图”,着名学者、《邓小平时代》译者冯克利先生十年治学思想笔记全新增订版。狄 马《一头自由主义的鹿》(说说底层,说说尊严,说说我们这个时代:青年先锋思想者狄马狮吼力作。
基本介绍
- 书名:梦路书系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页数:753页
- 开本:16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贺卫方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bkbkbi6495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梦路书系,取“梦想与路径”之意,书系秉持“独立之思想迎槓促,自由之精神”,不左不右不中庸,冀望在华语世界中,选取具有独立思考价值的文本,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做一套不仅讲述梦想更讲述路径与践行的书系,以期通过文本建设的努力,构戏愚院筑津梁,践行梦想。
对此,丛书策划者们如是说:
“保罗·高更创作的最大也最重视的一幅油画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古往今来,无数作者,无量文字,叙述和阐述的,大抵不外三件事:过去是怎幺回事,现在是什幺状态,将来该当如何。在我看来,尤关紧要的是:直面过去,踏实而稳健地构筑现在通往未来梦想的津梁和路径。”
对此,丛书策划者们如是说:
“保罗·高更创作的最大也最重视的一幅油画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古往今来,无数作者,无量文字,叙述和阐述的,大抵不外三件事:过去是怎幺回事,现在是什幺状态,将来该当如何。在我看来,尤关紧要的是:直面过去,踏实而稳健地构筑现在通往未来梦想的津梁和路径。”
作者简介
贺卫方,网名“守门老鹤”。家在山东牟平,近海,方言有特色。十八岁离家,远赴巴渝读法律,命运和口味都为之一变。曾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留中国政法大学,做不讲课的教师,编辑《比较法研究》。后转会北京大学,成为讲课的教师,编辑《中外法学》,偶尔发表点文章。很庆幸生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使自己这种既不喜官场气息又不懂经商之道还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
跨腿道冯克利,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山东青州长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内公认一流水準的翻译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代表作有译着《民主新论》、《乌合之众》、《立宪经济学》、《邓小平时代》等。
狄马,独立作家,青年先锋思想家。1970年出生于陕西子长县,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思想文化随笔、文学批评、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已出版思想文化随笔集《我们热爱什幺样的生活》、《另类童话》。
跨腿道冯克利,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山东青州长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内公认一流水準的翻译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代表作有译着《民主新论》、《乌合之众》、《立宪经济学》、《邓小平时代》等。
狄马,独立作家,青年先锋思想家。1970年出生于陕西子长县,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思想文化随笔、文学批评、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已出版思想文化随笔集《我们热爱什幺样的生活》、《另类童话》。
媒体推荐
贺卫方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但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身上折射出在当下中国急剧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的“合理冲突”,而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的价值就不仅仅在于法学界、在于法学研究,而应在更为宏大和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加以诠释。
——《经济观察报》
虽然至今尚未有什幺“公民学校”,但李慎之先生所说的“遥危妹汽公民教员”却逐渐出现,比如王小波和林达对一代人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所大学。相比之下,冯克利先生没有那幺高的公众知名度,在画地为牢的学院体制里也不算“大腕”。不过,他在公共思想界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仅告诉读者常识,还能从容走出学者的迷津。他的政治思想笔记《尤利西斯的自缚》也仿佛一剂中成药,道厦不是立竿见影,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显现出解毒的功效。
——自强资讯:《:为青春解毒,替常识说话》
与留着大鬍子的陕北汉子狄马相交多年,前年才在西安第一次见面。他不仅善写文章,而且会唱信天游,会说书。他的生活方式令人羡慕:悠闲中有执着,随意中有认真,如同他的文字。作为这个时代“废都”文化人中的异数,他的文章值得一读。
——学者 傅国涌
我断耻雄喜欢狄马,因为狄马的文章像民歌,有腔调。狄马的思想像金属,有响声。狄马的故事像先知,有信仰。狄马的脸庞像向日葵,不喜欢向黑暗的地方低头。
——学者 王怡
狄马的作品勇于挑战权威,抗拒时流,是血性文章却不失清明理性,很可一读。
——作家、学者 林贤治
我的思想启蒙老师是狄马先生。其实这世界的真相没那幺複杂和神秘,但某些人把它弄得云山雾罩,仿佛蒙着红盖头的娘们一般叵测。狄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地描绘出来,向你展示出真相。他的文章阿枣桨艰仿佛挑盖头的那个手指。这手指再向下,挑!真相再也绷不住了,它一笑,露出一嘴四环素牙。
——作家、设计师 张发财
应该承认,江湖传说的“狄马在写字人中唱歌最好,在唱歌人中写字最好”并非虚言。
——作家 宋石男
看到“狄马”我就想到“北狄”与“响马”,一睹风貌果然有几分匪气;文章也带“匪气”。狄马恰是“一头自由主义的鹿”。其人不仅陕北民歌唱得好,与此相通,深情地关注底层、关注民间、关注人性与人的权利,张扬自我的灵性,更是他写思想文化随笔一贯的追求。这种追求比他唱的“信天游”更长久地打动我的心弦。
——杂文家 鄢烈山
——《经济观察报》
虽然至今尚未有什幺“公民学校”,但李慎之先生所说的“遥危妹汽公民教员”却逐渐出现,比如王小波和林达对一代人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所大学。相比之下,冯克利先生没有那幺高的公众知名度,在画地为牢的学院体制里也不算“大腕”。不过,他在公共思想界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仅告诉读者常识,还能从容走出学者的迷津。他的政治思想笔记《尤利西斯的自缚》也仿佛一剂中成药,道厦不是立竿见影,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显现出解毒的功效。
——自强资讯:《:为青春解毒,替常识说话》
与留着大鬍子的陕北汉子狄马相交多年,前年才在西安第一次见面。他不仅善写文章,而且会唱信天游,会说书。他的生活方式令人羡慕:悠闲中有执着,随意中有认真,如同他的文字。作为这个时代“废都”文化人中的异数,他的文章值得一读。
——学者 傅国涌
我断耻雄喜欢狄马,因为狄马的文章像民歌,有腔调。狄马的思想像金属,有响声。狄马的故事像先知,有信仰。狄马的脸庞像向日葵,不喜欢向黑暗的地方低头。
——学者 王怡
狄马的作品勇于挑战权威,抗拒时流,是血性文章却不失清明理性,很可一读。
——作家、学者 林贤治
我的思想启蒙老师是狄马先生。其实这世界的真相没那幺複杂和神秘,但某些人把它弄得云山雾罩,仿佛蒙着红盖头的娘们一般叵测。狄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地描绘出来,向你展示出真相。他的文章阿枣桨艰仿佛挑盖头的那个手指。这手指再向下,挑!真相再也绷不住了,它一笑,露出一嘴四环素牙。
——作家、设计师 张发财
应该承认,江湖传说的“狄马在写字人中唱歌最好,在唱歌人中写字最好”并非虚言。
——作家 宋石男
看到“狄马”我就想到“北狄”与“响马”,一睹风貌果然有几分匪气;文章也带“匪气”。狄马恰是“一头自由主义的鹿”。其人不仅陕北民歌唱得好,与此相通,深情地关注底层、关注民间、关注人性与人的权利,张扬自我的灵性,更是他写思想文化随笔一贯的追求。这种追求比他唱的“信天游”更长久地打动我的心弦。
——杂文家 鄢烈山
图书目录
《逍遥法外》目录:
《梦路书系》总序
自序
辑一书中景色
做出版家真好
东京漫笔
台北访书记
香港访书二记
村上哲见及其《科举の书》
在胡适纪念馆
在英国法的圣殿里
狄更斯论法袍的效用
读《胡适留学日记》
歌德论治国之道
关于“和而不同”
《龙凤之国》
长城之用
萨维尼的矛盾
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辑二读史阅世
卫三畏与日本开国
李提摩太在牟平
消失了的墓地
使臣西洋看舞会
莫理循三题
容闳差点当律师
国政全凭议院施
拿破仑的治国理念
史学的力量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辑三话语千叶
汉语拼音文化断桥
说“拔凉”
方言拾零(一、二)
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口说髒话种芫荽
何事令我不得语
演讲以及阅读趣味的养成
部落格写作及其他
辑四士林观望
向胡适校长鞠躬
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
拜谒陈寅恪墓
朋友或告密者
有职有权的吴宓?
对知识分子的“优待”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
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学术引用规範与注释体例
对学术研究量化标準说不
走访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大学之道:内地与香港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大学里的大石头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里
六人
知识人扎堆儿说想像
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唯一价值
辑五逍遥无地
“文革”四十五周年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北京治堵策
“那事儿”究竟有无底限
“日记门”
一桩难题一个机遇
“虎照门”与真理的雪崩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红歌之忆
……
《一头自由主义的鹿》
《尤利西斯的自缚》
《梦路书系》总序
自序
辑一书中景色
做出版家真好
东京漫笔
台北访书记
香港访书二记
村上哲见及其《科举の书》
在胡适纪念馆
在英国法的圣殿里
狄更斯论法袍的效用
读《胡适留学日记》
歌德论治国之道
关于“和而不同”
《龙凤之国》
长城之用
萨维尼的矛盾
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辑二读史阅世
卫三畏与日本开国
李提摩太在牟平
消失了的墓地
使臣西洋看舞会
莫理循三题
容闳差点当律师
国政全凭议院施
拿破仑的治国理念
史学的力量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辑三话语千叶
汉语拼音文化断桥
说“拔凉”
方言拾零(一、二)
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口说髒话种芫荽
何事令我不得语
演讲以及阅读趣味的养成
部落格写作及其他
辑四士林观望
向胡适校长鞠躬
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
拜谒陈寅恪墓
朋友或告密者
有职有权的吴宓?
对知识分子的“优待”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
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学术引用规範与注释体例
对学术研究量化标準说不
走访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大学之道:内地与香港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大学里的大石头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里
六人
知识人扎堆儿说想像
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唯一价值
辑五逍遥无地
“文革”四十五周年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北京治堵策
“那事儿”究竟有无底限
“日记门”
一桩难题一个机遇
“虎照门”与真理的雪崩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红歌之忆
……
《一头自由主义的鹿》
《尤利西斯的自缚》
序言
《逍遥法外》贺卫方自序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余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2012年9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2012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幺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余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余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余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着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誌。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唯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乾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了一出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着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着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讚。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20世纪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乾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幺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贺卫方
2013年5月9日 于五道口新居
《尤利西斯的自缚》新版冯克利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若从最早一篇算起,时间跨度上有二十几年了,都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写下的介绍性文字。其中约一半篇目曾结集为《尤利西斯的自缚》,十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借这次机会,我把与译事无关的文章删去,又补上了十来篇近年所写的类似文章,以求体裁的统一,也算给读者有一个新的交待。蒙主编梁由之兄和责编周青丰兄不弃,这个半新半旧的增订本仍袭旧名,收入中信出版社《梦路书系》第一辑。
我自幼喜读杂书,有一本好书读的乐趣,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结束,因苦于无书可读,便又自学一点外语,从此有了为自己打开另一个阅读世界的可能。不过,我读书虽然既多且杂,从阅读中得到的感悟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长时间里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思想的消费者,并不敢动着述家的雄心。可是读到后来,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吧,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着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哈耶克等人的着作,便都是这种心情的产物。不过我最初确实未曾想到,此事会一发不可收拾。粗略统计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译的,与友人合译的,还有一些为他人校订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译书虽然还算勤奋,在写东西上我却是个地道的懒人。这期间写的所谓论文不能说没有,数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作一个译者,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为求读者理解的方便,在转换文字之外,总免不了要写一点绍介导读性的东西这,有时是逼着自己下笔,有时则是应媒体的朋友之邀。我不愿写文章虽是懒惰所至,但自忖念书尚不算愚钝,搭那些思想大师的便车,攀附于译作得有略施文墨的机会,还能赚得一点儿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这种搭别人便车的习惯虽不值得夸耀,也反映着我希望摆脱某种思想状态的过程。我这一代,或许还应算上比我更年长的一代中,由于时代的缘故,很多人被政治化的程度极深,关心政治几乎变得跟饮食男女一般自然。凡是过来人都知道,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政治于社会几乎无孔不入,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常常也会找上门来,这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印记。我每每见到一些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有何种职业背景,总喜欢议论时政,便是那个时代被过度政治化的结果。
从那个时代的话语气氛中薰陶出来的人,虽然不乏关心政治的热情,但至少以我个人的经历看,却不太明白什幺是政治。中国旧的价值体系历经百年摧残,早已土崩瓦解,挥洒春秋大义的空间一时大乱,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亏空,这使人们关心政治的本钱很贫乏。在那个单边政治笼罩一切,似乎只有迫害与被迫害决定着人间荣辱的时代,思想的热情往往也变得畸形。强势的一方只欲致对手于死地,不知对人可以求刑,观念却无法入罪,弱势的一方则情绪远远敏于知识。在这种强烈的对抗气氛中,无论贤与不肖,上下同求,观点貌似不两立,心态往往如出一辙。人们热衷于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要不在善恶的人格归属,而在制度安排能否对其有所增抑;不在理念之高远,而在如何让它无损体面地附着于人际。结果常如奥古斯丁所说,动机或不乏惩恶扬善,却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说谎者”。
为摆脱这种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认识和规範政治的话语,以完成“再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我愿意把一些着作译过来与人分享的动力之一。这些经我之手译过来的东西,除了《邓小平时代》有着比较複杂的动机——我在“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一文中已有所交待,此不赘——之外,从学科归属上看,尚不算驳杂,大都属于比较偏“右”的政经法一类。这既是我本人的阅读兴趣所致,也反映着近30年来中国文科重心从“红色经典”当家转向重新认识西学的过程。马基雅维里自不必说,如韦伯、勒庞、史蒂芬和哈耶克诸先贤,并不是多幺“前沿”的新学问,而是被我们一度视为与“人类进步”无涉,必欲扔出窗外而后快的东西。对于这种世风,我曾在《善善相争,无法不行》一文中,发过一番感慨。
若从更大的视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躁热过后,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保守与传统的思想氛围,我的阅读史大体也反映了自己是这股潮流不自觉的尾随者。中国人自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意识形态之战虽然远未终结,一方的自信已大为动摇,而另一方又找回了自己既往的价值。与清末民初时国人向世界开放时西人自承没落,精神陷入错乱乖戾的情况相比,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人谓卓有建树的改革运动,多是返本开新的结果,这于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30年来的大趋势,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起故纸堆来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东西,无论中西,现在又纷纷拣了回来。在今日的政治辩论中,以往贴有“右”、或“反动落后”一类标籤的东西,俨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思想生力军。
但是,思想的热络往往与其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换言之,炙炙之教,终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说,太平世道的人是不喜欢讲理论的,有那幺多人热衷于政治上的大概念和大叙事,乃社会危象的可靠徵兆。近年来中国的政治辩论有复兴之势,这或许是可喜之事。但西谚有云,趣味不争辩(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用,也可以反过来讲,争辩无趣味,各种话语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未尚不是一种社会危相的表现。复兴的背后,是未竟之功的焦虑。
当此之际,人也就无所逃于被贴上右派或左派这类意识形态标籤。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右”时,我也淡然处之。我相信左右只要缺了一端,俗世将变得十分跋扈,而教养是既可见于左,也可见于右的。只要讲规矩,明事理,左右无须取消,更不必超越,言行若能导之以规,这两造之争便能造福于国人。这大概是我读一些保守派经典时最深的感受。自由就像和平一样,是只在人际关係之间才有意义的概念,它的价值存在于对台戏之中。一家独占,不能让全体国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它或可为对抗提供道义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让各方通过竞争磨合,调适出一套公正的规则,以利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药,那属于无奈中选择的虎狼方,极易让政治变成“人不得不乾的髒活”,就像它也易于让人感觉到崇高与伟大一样。
其实,政治的崇高伟大和作为髒活之间,往往也就一线之隔。错乱之中,罪恶横行,人世间的无端之祸莫不缘此而生。柏拉图曾把我们人类称为“有皮无毛的双足动物”。但作为文明人,我们已不习惯于赤身裸体,总需要穿点什幺。为免干政治这一桩髒活污了我们有皮无毛的身子,就得穿一点思想观念的外衣。在这件事上,时尚的华服未必强过蓝缕。这个集子中的文字及其所介绍的着作,泰半也是我在读书过程中,从西学的故纸堆里打捞出来的。希望透它们,对那些不得不乾髒活的人,能够有所助益。
冯克利
2013年7月识于雀巢书斋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余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2012年9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2012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幺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余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余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余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着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誌。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唯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乾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了一出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着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着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讚。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20世纪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乾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幺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贺卫方
2013年5月9日 于五道口新居
《尤利西斯的自缚》新版冯克利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若从最早一篇算起,时间跨度上有二十几年了,都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写下的介绍性文字。其中约一半篇目曾结集为《尤利西斯的自缚》,十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借这次机会,我把与译事无关的文章删去,又补上了十来篇近年所写的类似文章,以求体裁的统一,也算给读者有一个新的交待。蒙主编梁由之兄和责编周青丰兄不弃,这个半新半旧的增订本仍袭旧名,收入中信出版社《梦路书系》第一辑。
我自幼喜读杂书,有一本好书读的乐趣,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结束,因苦于无书可读,便又自学一点外语,从此有了为自己打开另一个阅读世界的可能。不过,我读书虽然既多且杂,从阅读中得到的感悟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长时间里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思想的消费者,并不敢动着述家的雄心。可是读到后来,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吧,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着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哈耶克等人的着作,便都是这种心情的产物。不过我最初确实未曾想到,此事会一发不可收拾。粗略统计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译的,与友人合译的,还有一些为他人校订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译书虽然还算勤奋,在写东西上我却是个地道的懒人。这期间写的所谓论文不能说没有,数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作一个译者,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为求读者理解的方便,在转换文字之外,总免不了要写一点绍介导读性的东西这,有时是逼着自己下笔,有时则是应媒体的朋友之邀。我不愿写文章虽是懒惰所至,但自忖念书尚不算愚钝,搭那些思想大师的便车,攀附于译作得有略施文墨的机会,还能赚得一点儿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这种搭别人便车的习惯虽不值得夸耀,也反映着我希望摆脱某种思想状态的过程。我这一代,或许还应算上比我更年长的一代中,由于时代的缘故,很多人被政治化的程度极深,关心政治几乎变得跟饮食男女一般自然。凡是过来人都知道,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政治于社会几乎无孔不入,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常常也会找上门来,这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印记。我每每见到一些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有何种职业背景,总喜欢议论时政,便是那个时代被过度政治化的结果。
从那个时代的话语气氛中薰陶出来的人,虽然不乏关心政治的热情,但至少以我个人的经历看,却不太明白什幺是政治。中国旧的价值体系历经百年摧残,早已土崩瓦解,挥洒春秋大义的空间一时大乱,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亏空,这使人们关心政治的本钱很贫乏。在那个单边政治笼罩一切,似乎只有迫害与被迫害决定着人间荣辱的时代,思想的热情往往也变得畸形。强势的一方只欲致对手于死地,不知对人可以求刑,观念却无法入罪,弱势的一方则情绪远远敏于知识。在这种强烈的对抗气氛中,无论贤与不肖,上下同求,观点貌似不两立,心态往往如出一辙。人们热衷于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要不在善恶的人格归属,而在制度安排能否对其有所增抑;不在理念之高远,而在如何让它无损体面地附着于人际。结果常如奥古斯丁所说,动机或不乏惩恶扬善,却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说谎者”。
为摆脱这种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认识和规範政治的话语,以完成“再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我愿意把一些着作译过来与人分享的动力之一。这些经我之手译过来的东西,除了《邓小平时代》有着比较複杂的动机——我在“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一文中已有所交待,此不赘——之外,从学科归属上看,尚不算驳杂,大都属于比较偏“右”的政经法一类。这既是我本人的阅读兴趣所致,也反映着近30年来中国文科重心从“红色经典”当家转向重新认识西学的过程。马基雅维里自不必说,如韦伯、勒庞、史蒂芬和哈耶克诸先贤,并不是多幺“前沿”的新学问,而是被我们一度视为与“人类进步”无涉,必欲扔出窗外而后快的东西。对于这种世风,我曾在《善善相争,无法不行》一文中,发过一番感慨。
若从更大的视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躁热过后,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保守与传统的思想氛围,我的阅读史大体也反映了自己是这股潮流不自觉的尾随者。中国人自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意识形态之战虽然远未终结,一方的自信已大为动摇,而另一方又找回了自己既往的价值。与清末民初时国人向世界开放时西人自承没落,精神陷入错乱乖戾的情况相比,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人谓卓有建树的改革运动,多是返本开新的结果,这于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30年来的大趋势,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起故纸堆来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东西,无论中西,现在又纷纷拣了回来。在今日的政治辩论中,以往贴有“右”、或“反动落后”一类标籤的东西,俨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思想生力军。
但是,思想的热络往往与其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换言之,炙炙之教,终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说,太平世道的人是不喜欢讲理论的,有那幺多人热衷于政治上的大概念和大叙事,乃社会危象的可靠徵兆。近年来中国的政治辩论有复兴之势,这或许是可喜之事。但西谚有云,趣味不争辩(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用,也可以反过来讲,争辩无趣味,各种话语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未尚不是一种社会危相的表现。复兴的背后,是未竟之功的焦虑。
当此之际,人也就无所逃于被贴上右派或左派这类意识形态标籤。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右”时,我也淡然处之。我相信左右只要缺了一端,俗世将变得十分跋扈,而教养是既可见于左,也可见于右的。只要讲规矩,明事理,左右无须取消,更不必超越,言行若能导之以规,这两造之争便能造福于国人。这大概是我读一些保守派经典时最深的感受。自由就像和平一样,是只在人际关係之间才有意义的概念,它的价值存在于对台戏之中。一家独占,不能让全体国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它或可为对抗提供道义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让各方通过竞争磨合,调适出一套公正的规则,以利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药,那属于无奈中选择的虎狼方,极易让政治变成“人不得不乾的髒活”,就像它也易于让人感觉到崇高与伟大一样。
其实,政治的崇高伟大和作为髒活之间,往往也就一线之隔。错乱之中,罪恶横行,人世间的无端之祸莫不缘此而生。柏拉图曾把我们人类称为“有皮无毛的双足动物”。但作为文明人,我们已不习惯于赤身裸体,总需要穿点什幺。为免干政治这一桩髒活污了我们有皮无毛的身子,就得穿一点思想观念的外衣。在这件事上,时尚的华服未必强过蓝缕。这个集子中的文字及其所介绍的着作,泰半也是我在读书过程中,从西学的故纸堆里打捞出来的。希望透它们,对那些不得不乾髒活的人,能够有所助益。
冯克利
2013年7月识于雀巢书斋
图书目录
《逍遥法外》目录:
《梦路书系》总序
自序
辑一书中景色
做出版家真好
东京漫笔
台北访书记
香港访书二记
村上哲见及其《科举の书》
在胡适纪念馆
在英国法的圣殿里
狄更斯论法袍的效用
读《胡适留学日记》
歌德论治国之道
关于“和而不同”
《龙凤之国》
长城之用
萨维尼的矛盾
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辑二读史阅世
卫三畏与日本开国
李提摩太在牟平
消失了的墓地
使臣西洋看舞会
莫理循三题
容闳差点当律师
国政全凭议院施
拿破仑的治国理念
史学的力量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辑三话语千叶
汉语拼音文化断桥
说“拔凉”
方言拾零(一、二)
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口说髒话种芫荽
何事令我不得语
演讲以及阅读趣味的养成
部落格写作及其他
辑四士林观望
向胡适校长鞠躬
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
拜谒陈寅恪墓
朋友或告密者
有职有权的吴宓?
对知识分子的“优待”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
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学术引用规範与注释体例
对学术研究量化标準说不
走访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大学之道:内地与香港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大学里的大石头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里
六人
知识人扎堆儿说想像
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唯一价值
辑五逍遥无地
“文革”四十五周年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北京治堵策
“那事儿”究竟有无底限
“日记门”
一桩难题一个机遇
“虎照门”与真理的雪崩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红歌之忆
……
《一头自由主义的鹿》
《尤利西斯的自缚》
《梦路书系》总序
自序
辑一书中景色
做出版家真好
东京漫笔
台北访书记
香港访书二记
村上哲见及其《科举の书》
在胡适纪念馆
在英国法的圣殿里
狄更斯论法袍的效用
读《胡适留学日记》
歌德论治国之道
关于“和而不同”
《龙凤之国》
长城之用
萨维尼的矛盾
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辑二读史阅世
卫三畏与日本开国
李提摩太在牟平
消失了的墓地
使臣西洋看舞会
莫理循三题
容闳差点当律师
国政全凭议院施
拿破仑的治国理念
史学的力量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辑三话语千叶
汉语拼音文化断桥
说“拔凉”
方言拾零(一、二)
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口说髒话种芫荽
何事令我不得语
演讲以及阅读趣味的养成
部落格写作及其他
辑四士林观望
向胡适校长鞠躬
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
拜谒陈寅恪墓
朋友或告密者
有职有权的吴宓?
对知识分子的“优待”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
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学术引用规範与注释体例
对学术研究量化标準说不
走访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大学之道:内地与香港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大学里的大石头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里
六人
知识人扎堆儿说想像
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唯一价值
辑五逍遥无地
“文革”四十五周年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北京治堵策
“那事儿”究竟有无底限
“日记门”
一桩难题一个机遇
“虎照门”与真理的雪崩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红歌之忆
……
《一头自由主义的鹿》
《尤利西斯的自缚》
序言
《逍遥法外》贺卫方自序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余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2012年9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2012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幺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余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余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余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着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誌。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唯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乾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了一出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着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着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讚。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20世纪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乾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幺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贺卫方
2013年5月9日 于五道口新居
《尤利西斯的自缚》新版冯克利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若从最早一篇算起,时间跨度上有二十几年了,都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写下的介绍性文字。其中约一半篇目曾结集为《尤利西斯的自缚》,十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借这次机会,我把与译事无关的文章删去,又补上了十来篇近年所写的类似文章,以求体裁的统一,也算给读者有一个新的交待。蒙主编梁由之兄和责编周青丰兄不弃,这个半新半旧的增订本仍袭旧名,收入中信出版社《梦路书系》第一辑。
我自幼喜读杂书,有一本好书读的乐趣,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结束,因苦于无书可读,便又自学一点外语,从此有了为自己打开另一个阅读世界的可能。不过,我读书虽然既多且杂,从阅读中得到的感悟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长时间里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思想的消费者,并不敢动着述家的雄心。可是读到后来,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吧,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着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哈耶克等人的着作,便都是这种心情的产物。不过我最初确实未曾想到,此事会一发不可收拾。粗略统计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译的,与友人合译的,还有一些为他人校订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译书虽然还算勤奋,在写东西上我却是个地道的懒人。这期间写的所谓论文不能说没有,数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作一个译者,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为求读者理解的方便,在转换文字之外,总免不了要写一点绍介导读性的东西这,有时是逼着自己下笔,有时则是应媒体的朋友之邀。我不愿写文章虽是懒惰所至,但自忖念书尚不算愚钝,搭那些思想大师的便车,攀附于译作得有略施文墨的机会,还能赚得一点儿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这种搭别人便车的习惯虽不值得夸耀,也反映着我希望摆脱某种思想状态的过程。我这一代,或许还应算上比我更年长的一代中,由于时代的缘故,很多人被政治化的程度极深,关心政治几乎变得跟饮食男女一般自然。凡是过来人都知道,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政治于社会几乎无孔不入,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常常也会找上门来,这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印记。我每每见到一些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有何种职业背景,总喜欢议论时政,便是那个时代被过度政治化的结果。
从那个时代的话语气氛中薰陶出来的人,虽然不乏关心政治的热情,但至少以我个人的经历看,却不太明白什幺是政治。中国旧的价值体系历经百年摧残,早已土崩瓦解,挥洒春秋大义的空间一时大乱,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亏空,这使人们关心政治的本钱很贫乏。在那个单边政治笼罩一切,似乎只有迫害与被迫害决定着人间荣辱的时代,思想的热情往往也变得畸形。强势的一方只欲致对手于死地,不知对人可以求刑,观念却无法入罪,弱势的一方则情绪远远敏于知识。在这种强烈的对抗气氛中,无论贤与不肖,上下同求,观点貌似不两立,心态往往如出一辙。人们热衷于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要不在善恶的人格归属,而在制度安排能否对其有所增抑;不在理念之高远,而在如何让它无损体面地附着于人际。结果常如奥古斯丁所说,动机或不乏惩恶扬善,却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说谎者”。
为摆脱这种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认识和规範政治的话语,以完成“再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我愿意把一些着作译过来与人分享的动力之一。这些经我之手译过来的东西,除了《邓小平时代》有着比较複杂的动机——我在“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一文中已有所交待,此不赘——之外,从学科归属上看,尚不算驳杂,大都属于比较偏“右”的政经法一类。这既是我本人的阅读兴趣所致,也反映着近30年来中国文科重心从“红色经典”当家转向重新认识西学的过程。马基雅维里自不必说,如韦伯、勒庞、史蒂芬和哈耶克诸先贤,并不是多幺“前沿”的新学问,而是被我们一度视为与“人类进步”无涉,必欲扔出窗外而后快的东西。对于这种世风,我曾在《善善相争,无法不行》一文中,发过一番感慨。
若从更大的视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躁热过后,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保守与传统的思想氛围,我的阅读史大体也反映了自己是这股潮流不自觉的尾随者。中国人自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意识形态之战虽然远未终结,一方的自信已大为动摇,而另一方又找回了自己既往的价值。与清末民初时国人向世界开放时西人自承没落,精神陷入错乱乖戾的情况相比,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人谓卓有建树的改革运动,多是返本开新的结果,这于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30年来的大趋势,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起故纸堆来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东西,无论中西,现在又纷纷拣了回来。在今日的政治辩论中,以往贴有“右”、或“反动落后”一类标籤的东西,俨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思想生力军。
但是,思想的热络往往与其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换言之,炙炙之教,终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说,太平世道的人是不喜欢讲理论的,有那幺多人热衷于政治上的大概念和大叙事,乃社会危象的可靠徵兆。近年来中国的政治辩论有复兴之势,这或许是可喜之事。但西谚有云,趣味不争辩(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用,也可以反过来讲,争辩无趣味,各种话语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未尚不是一种社会危相的表现。复兴的背后,是未竟之功的焦虑。
当此之际,人也就无所逃于被贴上右派或左派这类意识形态标籤。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右”时,我也淡然处之。我相信左右只要缺了一端,俗世将变得十分跋扈,而教养是既可见于左,也可见于右的。只要讲规矩,明事理,左右无须取消,更不必超越,言行若能导之以规,这两造之争便能造福于国人。这大概是我读一些保守派经典时最深的感受。自由就像和平一样,是只在人际关係之间才有意义的概念,它的价值存在于对台戏之中。一家独占,不能让全体国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它或可为对抗提供道义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让各方通过竞争磨合,调适出一套公正的规则,以利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药,那属于无奈中选择的虎狼方,极易让政治变成“人不得不乾的髒活”,就像它也易于让人感觉到崇高与伟大一样。
其实,政治的崇高伟大和作为髒活之间,往往也就一线之隔。错乱之中,罪恶横行,人世间的无端之祸莫不缘此而生。柏拉图曾把我们人类称为“有皮无毛的双足动物”。但作为文明人,我们已不习惯于赤身裸体,总需要穿点什幺。为免干政治这一桩髒活污了我们有皮无毛的身子,就得穿一点思想观念的外衣。在这件事上,时尚的华服未必强过蓝缕。这个集子中的文字及其所介绍的着作,泰半也是我在读书过程中,从西学的故纸堆里打捞出来的。希望透它们,对那些不得不乾髒活的人,能够有所助益。
冯克利
2013年7月识于雀巢书斋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余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2012年9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2012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幺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余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余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余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着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誌。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唯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乾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了一出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着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着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讚。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20世纪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乾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幺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贺卫方
2013年5月9日 于五道口新居
《尤利西斯的自缚》新版冯克利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若从最早一篇算起,时间跨度上有二十几年了,都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写下的介绍性文字。其中约一半篇目曾结集为《尤利西斯的自缚》,十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借这次机会,我把与译事无关的文章删去,又补上了十来篇近年所写的类似文章,以求体裁的统一,也算给读者有一个新的交待。蒙主编梁由之兄和责编周青丰兄不弃,这个半新半旧的增订本仍袭旧名,收入中信出版社《梦路书系》第一辑。
我自幼喜读杂书,有一本好书读的乐趣,一向是来者不拒的。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结束,因苦于无书可读,便又自学一点外语,从此有了为自己打开另一个阅读世界的可能。不过,我读书虽然既多且杂,从阅读中得到的感悟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因才情不逮,很长时间里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思想的消费者,并不敢动着述家的雄心。可是读到后来,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吧,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着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哈耶克等人的着作,便都是这种心情的产物。不过我最初确实未曾想到,此事会一发不可收拾。粗略统计了一下,如果把自己译的,与友人合译的,还有一些为他人校订的都算上,竟已有二十多本。
译书虽然还算勤奋,在写东西上我却是个地道的懒人。这期间写的所谓论文不能说没有,数量也很少。然而即便只作一个译者,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为求读者理解的方便,在转换文字之外,总免不了要写一点绍介导读性的东西这,有时是逼着自己下笔,有时则是应媒体的朋友之邀。我不愿写文章虽是懒惰所至,但自忖念书尚不算愚钝,搭那些思想大师的便车,攀附于译作得有略施文墨的机会,还能赚得一点儿文名,可以算是傻人有傻福。
这种搭别人便车的习惯虽不值得夸耀,也反映着我希望摆脱某种思想状态的过程。我这一代,或许还应算上比我更年长的一代中,由于时代的缘故,很多人被政治化的程度极深,关心政治几乎变得跟饮食男女一般自然。凡是过来人都知道,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政治于社会几乎无孔不入,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常常也会找上门来,这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印记。我每每见到一些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有何种职业背景,总喜欢议论时政,便是那个时代被过度政治化的结果。
从那个时代的话语气氛中薰陶出来的人,虽然不乏关心政治的热情,但至少以我个人的经历看,却不太明白什幺是政治。中国旧的价值体系历经百年摧残,早已土崩瓦解,挥洒春秋大义的空间一时大乱,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亏空,这使人们关心政治的本钱很贫乏。在那个单边政治笼罩一切,似乎只有迫害与被迫害决定着人间荣辱的时代,思想的热情往往也变得畸形。强势的一方只欲致对手于死地,不知对人可以求刑,观念却无法入罪,弱势的一方则情绪远远敏于知识。在这种强烈的对抗气氛中,无论贤与不肖,上下同求,观点貌似不两立,心态往往如出一辙。人们热衷于臧否人物,不察世事之良窳,要不在善恶的人格归属,而在制度安排能否对其有所增抑;不在理念之高远,而在如何让它无损体面地附着于人际。结果常如奥古斯丁所说,动机或不乏惩恶扬善,却都成了“情不自禁的说谎者”。
为摆脱这种窘境,便需要一些重新认识和规範政治的话语,以完成“再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我愿意把一些着作译过来与人分享的动力之一。这些经我之手译过来的东西,除了《邓小平时代》有着比较複杂的动机——我在“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一文中已有所交待,此不赘——之外,从学科归属上看,尚不算驳杂,大都属于比较偏“右”的政经法一类。这既是我本人的阅读兴趣所致,也反映着近30年来中国文科重心从“红色经典”当家转向重新认识西学的过程。马基雅维里自不必说,如韦伯、勒庞、史蒂芬和哈耶克诸先贤,并不是多幺“前沿”的新学问,而是被我们一度视为与“人类进步”无涉,必欲扔出窗外而后快的东西。对于这种世风,我曾在《善善相争,无法不行》一文中,发过一番感慨。
若从更大的视角看,西方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躁热过后,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保守与传统的思想氛围,我的阅读史大体也反映了自己是这股潮流不自觉的尾随者。中国人自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意识形态之战虽然远未终结,一方的自信已大为动摇,而另一方又找回了自己既往的价值。与清末民初时国人向世界开放时西人自承没落,精神陷入错乱乖戾的情况相比,这大概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人谓卓有建树的改革运动,多是返本开新的结果,这于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30年来的大趋势,便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起故纸堆来了,先前被扔到窗外的东西,无论中西,现在又纷纷拣了回来。在今日的政治辩论中,以往贴有“右”、或“反动落后”一类标籤的东西,俨然又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思想生力军。
但是,思想的热络往往与其深刻成反比。老子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换言之,炙炙之教,终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所以埃德蒙·柏克说,太平世道的人是不喜欢讲理论的,有那幺多人热衷于政治上的大概念和大叙事,乃社会危象的可靠徵兆。近年来中国的政治辩论有复兴之势,这或许是可喜之事。但西谚有云,趣味不争辩(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用,也可以反过来讲,争辩无趣味,各种话语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未尚不是一种社会危相的表现。复兴的背后,是未竟之功的焦虑。
当此之际,人也就无所逃于被贴上右派或左派这类意识形态标籤。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右”时,我也淡然处之。我相信左右只要缺了一端,俗世将变得十分跋扈,而教养是既可见于左,也可见于右的。只要讲规矩,明事理,左右无须取消,更不必超越,言行若能导之以规,这两造之争便能造福于国人。这大概是我读一些保守派经典时最深的感受。自由就像和平一样,是只在人际关係之间才有意义的概念,它的价值存在于对台戏之中。一家独占,不能让全体国民一起分享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它或可为对抗提供道义支持,但它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功用,是让各方通过竞争磨合,调适出一套公正的规则,以利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如果自由精神被逼成治世的猛药,那属于无奈中选择的虎狼方,极易让政治变成“人不得不乾的髒活”,就像它也易于让人感觉到崇高与伟大一样。
其实,政治的崇高伟大和作为髒活之间,往往也就一线之隔。错乱之中,罪恶横行,人世间的无端之祸莫不缘此而生。柏拉图曾把我们人类称为“有皮无毛的双足动物”。但作为文明人,我们已不习惯于赤身裸体,总需要穿点什幺。为免干政治这一桩髒活污了我们有皮无毛的身子,就得穿一点思想观念的外衣。在这件事上,时尚的华服未必强过蓝缕。这个集子中的文字及其所介绍的着作,泰半也是我在读书过程中,从西学的故纸堆里打捞出来的。希望透它们,对那些不得不乾髒活的人,能够有所助益。
冯克利
2013年7月识于雀巢书斋
 累积网新闻资讯
累积网新闻资讯